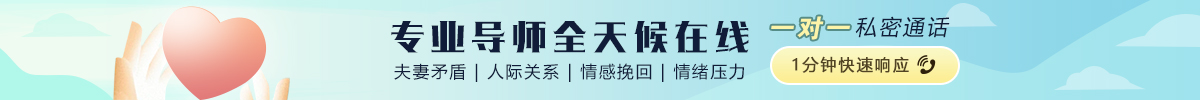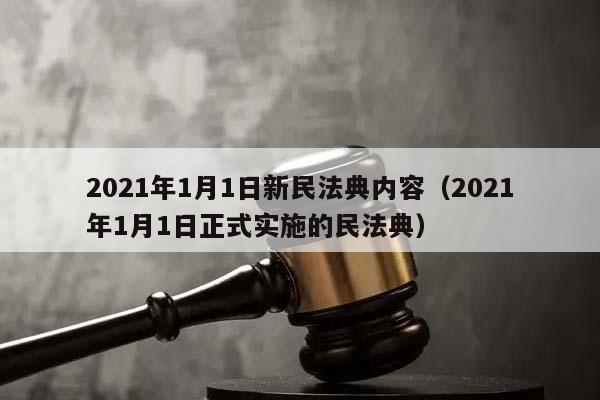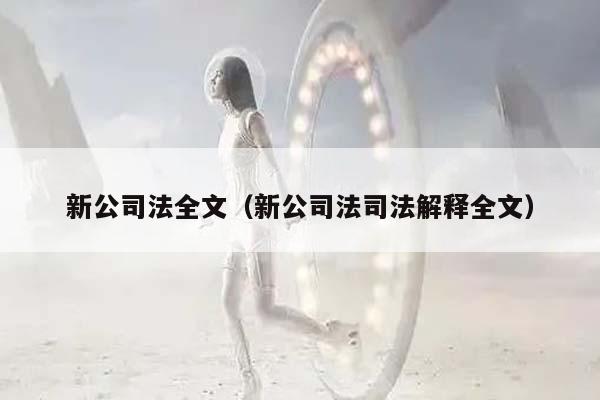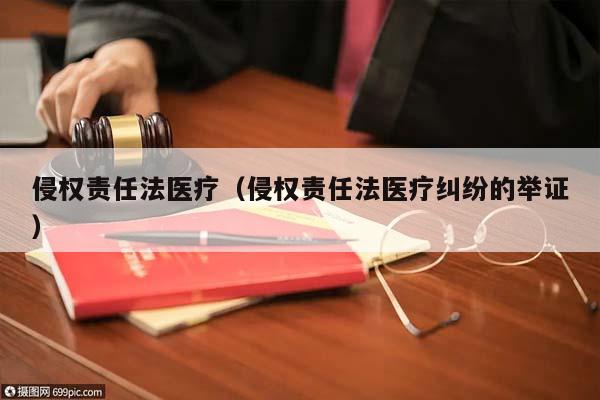未遂犯罪的量刑原则与标准 刑法视角下犯罪未遂怎么量刑
当犯罪分子已果敢地迈出实施犯罪的脚步,却因诸如被害人的奋力反抗、意外状况的横生等自身意志以外的阻碍,未能将犯罪推进至既遂阶段,此时,未遂犯罪的认定与量刑便成为司法实践与理论探讨的关键议题。

一、犯罪未遂量刑的基本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一规定为犯罪未遂的量刑奠定了基石。从法律条文来看,“可以” 表明法官在量刑时有一定自由裁量权,并非必须从轻或减轻处罚。例如在某些盗窃未遂案件中,若犯罪分子虽未成功窃取财物,但实施盗窃行为时手段恶劣,对公私财物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法官有可能基于案件具体情况,不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该条文强调了犯罪未遂与既遂在量刑上的关联,即未遂犯量刑以既遂犯为参照标准,这体现了刑法对不同犯罪形态的合理区分与惩处。
二、影响犯
罪未遂量的关键因素刑犯罪性质严重程度:不同性质犯罪的未遂量刑差异明显。暴力性犯罪如故意杀人未遂与非暴力性犯罪如盗窃未遂相比,由于前者对公民人身安全威胁巨大,即便未遂,其量刑起点往往也高于盗窃未遂。在故意杀人未遂案件中,若行为人持刀对他人实施杀害行为,虽因他人反抗等意志以外原因未造成死亡结果,但因其行为的极端危险性,量刑通常较重。而盗窃未遂案件中,若盗窃金额较小且未遂情节轻微,可能量刑相对较轻。
犯罪行为的进展程度:犯罪行为越接近既遂状态,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越大,量刑时从轻或减轻幅度越小。例如在诈骗未遂案件中,若行为人已完成诈骗的全部流程,仅因最后转账环节被识破而未得逞,其行为进展程度高,与刚着手实施诈骗就被发现的情况相比,前者量刑时从轻幅度会更小。因为前者对公私财产安全造成的现实危险更紧迫,社会危害性更大。
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主观恶性体现在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方面。若犯罪分子犯罪动机恶劣,如为报复他人而实施故意伤害未遂,且事后毫无悔意,在量刑时从轻或减轻的可能性就小。相反,若犯罪动机相对较轻,如因生活所迫临时起意盗窃未遂,且犯罪后主动坦白、积极悔罪,法官在量刑时会更多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特殊类型犯罪未遂的量刑考量
经济犯罪中的未遂量刑:在经济犯罪领域,如贪污、受贿未遂案件,量刑时不仅要考虑犯罪金额,还要考虑犯罪行为对国家经济秩序、公职人员廉洁性的破坏程度。以受贿未遂为例,若国家工作人员已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开始实施具体的权钱交易行为,只是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实际收受财物,在量刑时会综合其职位高低、可能造成的利益输送规模等因素。如果其职位关键,一旦受贿得逞可能对公共资源分配、项目审批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即便未遂,量刑也会相对较重。
危险犯的未遂量刑:危险犯是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如破坏交通工具罪、放火罪等。在这些犯罪的未遂情形中,重点考量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程度。例如,行为人在铁轨上放置障碍物企图使火车倾覆,虽因及时被发现清除未造成火车实际倾覆,但已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险,在量刑时虽可参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由于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从轻或减轻幅度可能有限。
四、犯罪未遂与其他犯罪形态量刑的比较与协调
与犯罪预备量刑比较:犯罪预备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阶段,尚未着手实行犯罪。相比犯罪未遂,犯罪预备的社会危害性更小,因为其对法益的威胁尚未达到紧迫程度。在量刑上,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犯罪未遂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通常犯罪预备的量刑会轻于犯罪未遂。例如,为实施抢劫而购买刀具、踩点,但尚未进入抢劫现场就被发现的犯罪预备行为,与进入抢劫现场已着手实施抢劫但因被害人反抗未得逞的犯罪未遂行为相比,前者量刑更轻。
与犯罪中止量刑协调:犯罪中止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犯罪中止体现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的降低以及对法益侵害的主动避免,与犯罪未遂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有本质区别。在量刑协调上,犯罪中止的处罚明显轻于犯罪未遂,这有助于鼓励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及时悬崖勒马,减少社会危害。例如,行为人在实施故意杀人过程中,因良心发现自动放弃杀人行为且未造成任何损害的,应免除处罚;而若因他人阻止等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故意杀人未遂,即便从轻或减轻处罚,也不会免除处罚 。
文章版权声明:除非注明,否则均为 六尺法律咨询网 原创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